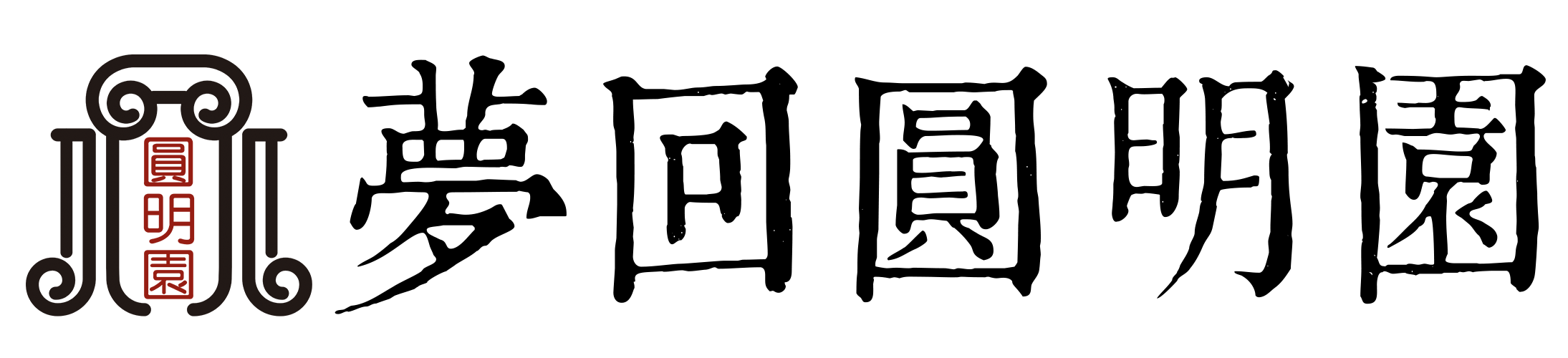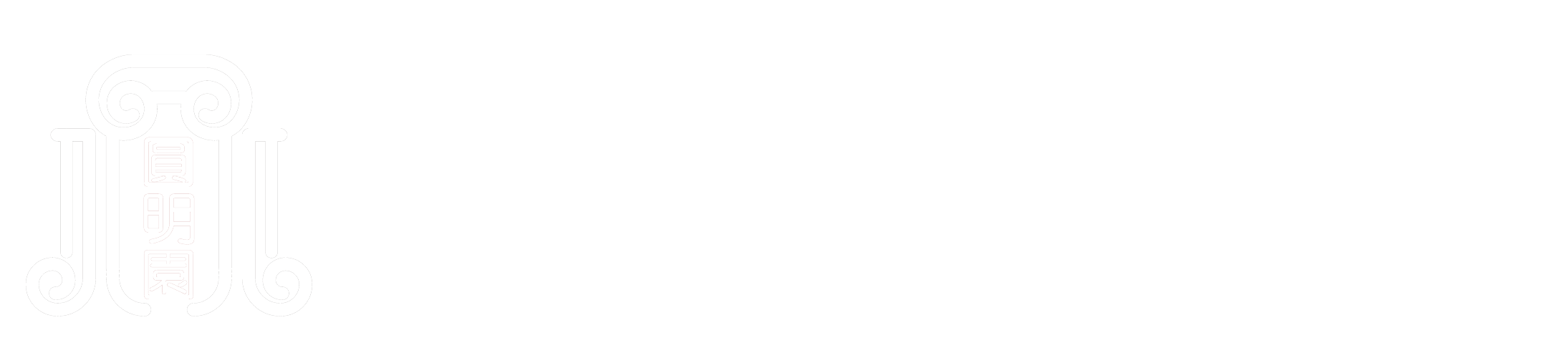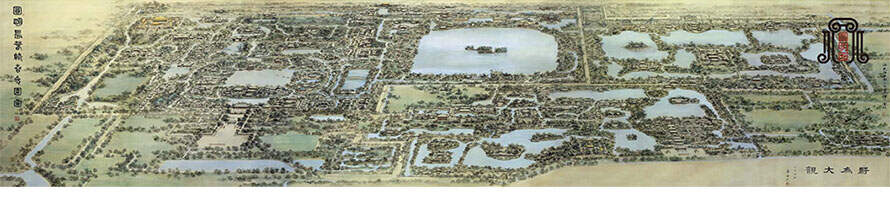沿着中关村大道向北,从北大南门,绕到北大西门,再往前,经一0一中学左拐,至达园宾馆门口,有一条右转的小路,往里走大约五百米左右,便能看一个村子,这,就是当年闻名遐迩的“圆明园画家村”。
现在这个地方早已经荡然无存,大都被拆迁,筑起了围墙。但在十多年以前,这里还有着密密麻麻“住不完的小平房”(诗人俞心樵语)。那些高低不平的院墙与错落有致的房屋,就趴在圆明园废墟的遗址之上,据说,最先也是由一些流落到北京的外地移民所建。20世纪50年代末,国家开始实行户籍制管理,政府把这一带的自然村落与游散的居民圈起来,分成了福缘门和圆明园两个行政村。若干年前,我和许多画家朋友,主要是居住于福缘门村,而并非外界谈论的圆明园村。但是,由于福缘门村就坐落在圆明园废墟之上,且跟圆明园村首尾相连,不分彼此,所以,外界更愿意将我们当年所居住的福缘门,说成是“圆明园画家村”。
将圆明园废墟作为某种象征,包含了文化复兴的宏愿。废墟中夹带着历史的沧桑,往往也孕育着重建的冲动。雅典的提修斯神庙,法国的阿尔勒剧场和圆形竞技场,德国的特里夫斯公共浴池,西班牙的塞哥维亚引水渡槽,以及葡萄牙的埃武拉神殿,等等,虽然后来都成了废墟,但它们作为某种文化标志,却为欧洲的文艺复兴,注入了历史的能量。圆明园废墟也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,因为它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屈受辱的历史,所以,它作为一种凭吊古迹,也就成了我们痛定思痛、百废待兴的象征物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政府一直保留着圆明园废墟,并把它规划成公园的原因。
事实上,中国的现代文化及其现代艺术进程,跟圆明园废墟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,北岛和芒克等北京诗人,就曾以《今天》杂志的名义,在圆明园遗址上组织过诗歌朗诵会;稍晚一点,又有北京画家林春岩,以“印象派”风格,在此创作了不少关于废墟题材的绘画;而与林春岩同一时期的北京诗人黑大春,还曾租居于此,创作了诸如《圆明园酒鬼》等许多跟圆明园意向有关的名诗……正是这些人的艺术创作与文化活动,为后来的“圆明园画家村”作了历史铺垫,也为其植下了现代文化的精神种子。
20世纪80年代末,先后毕业于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,如华庆、张大力、牟森、高波、张念、康木等人,主动放弃国家分配,以“盲流”身份,寄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娄斗桥一带,成了京城较早的一批流浪艺术家。吴文光早年拍摄的电影《流浪北京》,纪录了他们当年的一些生活状态。尽管这些人后来大都踏出国门,去了海外发展,但他们那种自由择业的勇气,却撼动了户籍制度的基石,为后来更多的艺术家流浪北京,选择自由职业,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。尤其是他们均都寄住在圆明园附近,以此为创作和生活的据点,也就拉开了“圆明园画家村”的历史帷幕。

当年“圆明园画家村”的内部景象。
1990年,曾经参与报道流浪艺术家的《中国美术报》原编辑人员田彬、丁方等人,因其报社解体,纷纷撤退出来,与先前搬到附近的方力钧、伊灵等艺术家,一起迁入福缘门村,从而形成了一个艺术家集聚的中心。这就是“圆明园画家村”的雏形。此后,随着越来越多流浪艺术家纷至沓来,也吸引了许多媒体的关注。于是,“圆明园画家村”的称呼,不胫而走,逐渐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。
我到“圆明园画家村”,是1993年春。那时的福缘门,已经集聚了几十位艺术家,我在那里居住了两年半时间,至1995年,据说,艺术家人数已达到了三四百。我虽然没有对“圆明园画家村”的艺术家人数做过具体统计,但确实感受过那种摩肩接踵、熙来攘往的热闹场面。在我的印象中,那时候的福缘门,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艺术家居住,甚至还有许多房东干脆搬到别处,将自己的房子全部腾出来租给艺术家。现在回想起来,还真觉得那时候的福缘门,有点像世外桃源。我甚至都不敢往下想,如果“圆明园画家村”不在1995年解散,按当时的情形发展下去,到底会是什么样子?也许一切都是必然,就像人的生理周期,青春期有骚动,而人到中年,就会变得沉着冷静。福缘门留下来的,正是我们这一批人青春走过的痕迹,也必然会把我们这批人重新送向各自的征程……
回头再来谈论“圆明园画家村”,我更喜欢把它看成是理想主义的产物。尽管那时候的福缘门,也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,且充满了商业的气味,但就其流浪的性质而言,却是源于人性解放的冲动与理想。事实上,也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来临,将中国的历史从过去禁锢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,才使人们有了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的可能。如果没有商业社会的大环境,不可能出现“圆明园画家村”,当然,也就更不可能出现后来各种各样的艺术家村落与艺术区现象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圆明园画家村”恰恰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转折,它终结的是过去意识形态的桎梏,开启的是后来经济与人格的自立。
我现在还保留着一份当年由画家王秋人执笔的《圆明园艺术村自由艺术家宣言》,其中有这样一段豪言壮语:“黎明前的地平线上的曙光已慢慢升起,照耀在我们的精神之路上。一种新的生存形式已在华夏大地上的古老而残败的冈林上确立!”将生存方式以文化的高度,借助于宣言的形式提出来,是“圆明园画家村”的首开风气。它反拨了当时某些学院派的观点,即“圆明园画家村”只有生活没有艺术,恰恰是对“五四”启蒙思想的继承与深化。我这么说,并不是夸大“圆明园画家村”的价值,而是任何文化活动如果落实不到自由的生命个体上,都只会成为对某种利益集团的维护。事实证明,“圆明园画家村”的生活方式,的确成了启蒙思潮的一部分。因为只有在“圆明园画家村”之后,我们才看到了中国有大批职业艺术家的出现,看到了现代艺术家的生存方式。
历史是由一代一代人建构起来的,克罗奇说的“一切古代史即是当代史”的命题,恰恰证明了当代是历史创造的结果。所以,朱熹说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这里说的源头活水,指的就是一种文化的青春与活力。“圆明园画家村”象征了某种文化的青春期。虽然当年它还很稚嫩,不可能有所作为,但却蕴藏了一批人的青春热血,也包含了一批人的理想冲动。正是这种青春热血与理想冲动,使得那片满目疮痍的圆明园废墟,重新焕发出生机,孕育出了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与艺术精神。
我始终觉得,“圆明园画家村”的意义,并不在地理概念的过去,而是落在了未来的生命形态上。其文化价值,也绝不会因为它的消失而冲淡。相反,只会随着历史时空的转换,而不断突显;会随着我们这批从中走出来的生命个体,在人生和艺术上的种种作为,而日益扩大。
文/杨卫
2005.10.8于通州
2020.4.15改于通州